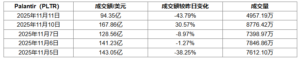作曲家 Max Marcoll:“AI 是它自己的监狱。我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打破栏杆
快速阅读: 据《爱尔兰时报》最新报道,德国作曲家马克斯米利安·马科尔将参加爱尔兰“音乐之流”音乐节,其作品《挪用放大VI》包含未经修改的文艺复兴合唱音乐。马科尔探讨社会议题,质疑AI在创意领域的角色,强调人类作曲家应突破传统框架。4月24日他将举办讲座。
马克斯米利安·马科尔通过结合“挪用”和“放大”创造了“挪用放大”这个词。爱尔兰观众将在本月的“音乐之流”音乐节上,通过聆听这位德国作曲家的作品,确切地了解这听起来是什么样子——但鉴于他的作品《挪用放大VI》包含了一段未经任何改动的帕莱斯特里纳文艺复兴合唱音乐杰作《教皇马塞卢斯弥撒》的现场表演,你可以看到他所追求的方向。马科尔出生在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吕贝克,是一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的作曲家。在他的作品中,他探讨了社会不平等以及音乐作为囚犯酷刑工具等问题。2017年,原定在五旬节周末柏林户外首演的《宣礼:三重挪用》因担心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而被取消。马科尔希望“以一个手势象征性地融合三种宗教:在原本属于犹太人的节日里,宣礼声——宣礼员的祈祷召唤——从塔楼传出”,并伴有钟琴声。取消演出是因为害怕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攻击。对此,马科尔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我对取消首演感到非常沮丧,但这与其说是一次个人和艺术上的失望,不如说是一次社会上的失败。在我看来,这里的自我审查是一种过早的顺从行为,一种对争议话题的怯懦回避,不幸的是,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多元文化主义反对者的胜利。”
马科尔的政治参与始于他在埃森福克旺艺术大学学习生涯的尾声。他有一个“不公平”的想法,认为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彻头彻尾的胆小鬼,因为我们窗外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所做的毫无关系。我发现这极其可耻,所以我必须找到改变的方法,至少要从自己做起。我想这就是我开始在艺术语境中参与政治的起点。”
他解释说,《挪用放大》系列作品的想法来源于对知识产权、发明概念等的思考。“我真的喜欢成为这样一位作曲家,创作出不仅仅是单独存在的音乐作品。在《挪用放大》中,可以说没有一个音符——我们甚至不需要使用‘发明’这个术语——是我自己创造的。里面百分之百的声音都来自其他作曲家。我只是退后一步,只存在于创造——另一个可以争论的术语——这种过滤网格之中,无论你如何称呼它,它就像是叠加在原始作品之上的一种东西。”
帕莱斯特里纳作品的表演者,爱尔兰声乐团体Tonnta,生活在与他将对其演唱进行电子处理截然不同的宇宙中,“从几乎听不见的缓慢渐变到极其快速且残酷的切割”。他说,所有这些“也许只是从知识产权和电子设备角色的思考中得出的一个自然延续步骤。同时也关于档案馆及其处理方式的思考——如何复活已存在的作品并将它们作为素材。‘材料’的概念意味着它是未完成的或者需要准备的东西,就像烹饪中的食材一样——一根胡萝卜永远不可能单独构成一顿饭;它需要被加工。
“我的想法是把整部作品当作材料,完全不作任何改动。这让我非常着迷:材料不是未完成的东西,也不是需要首先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你想到木头,木头并不是凭空存在的。它需要通过砍伐树木并将其分割来创造。材料是一种未完成但经过培育的东西。然后更进一步地说,‘不,我要拿整个作品,这就是我的材料。’一件已经完整无缺的艺术品。”
在《挪用放大》之外,“这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喜欢创作一系列作品。在一个名为《化合物》的系列中,材料是我的日常生活录音。在《坚果/乳酪》系列中,其中一个将在音乐节上首演,是非常非常慢的脉冲。”
马克斯米利安·马科尔说他喜欢“运用非常简单的应用,并尝试扭曲它们,从中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特别喜欢的是“拿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应用程序,尝试扭曲它们并从中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东西。从技术角度看,《挪用放大》中所做之事可能是使用电子设备能够实现的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只是振幅调制。你只需将推子推高再拉低即可完成。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在195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能做到。我喜欢那些过时的东西,并用它们来展示我们实际上还没有理解这些东西能做什么。对于最新的技术潮流,我持怀疑和警惕态度。”
“AI的奇怪之处在于,它内部发生的一切以及将来都会是一个黑箱。我们无法进入并以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改变事物。即使是创造这些模型的程序员自己也无法进去,因为这就是它的理念。它的理念是一个自我组织的网络,通过数据训练并以某种方式表现。但我们不能进入电路并以一种我们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的方式改变事物。你无法阅读它,也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操纵它。这是一个完全的黑箱,对我来说这使得它完全无趣。”
“我可以使用AI工具。我对偶尔从有能力的助手那里获得帮助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从创意角度看,目前我对此不感兴趣。我为一支大乐队和一个小管弦乐队创作了一首作品,我们将1960年代的爵士三重奏编排输入机器。得到了很多非常疯狂的爵士风格的东西。我喜欢玩弄它并创造破碎的陈词滥调中的陈词滥调之类的东西。对于那首作品来说,它确实有效。但目前我没有内在的兴趣去处理这个完全封闭且不透明的实体。”
马科尔回到遗传学的类比。“发现的时刻是人类第一次解码DNA。如果你想了解哪个基因负责什么功能或身体的哪一部分,就像一个试错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什么负责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DNA每秒都在变化,那就去做这个。因为这就是AI的理念。你有一个学习的网络,每次实例都完全不同。每次我教它新的东西,这个网络都会变得完全不同。
“在此意义上,‘黑客’意味着你进入其中解读这个庞大序列中的所有基因,并找出临界空间中哪个参数负责什么功能。这不是人类可读的代码,你无法确定这里的数字应该是什么。”
他是否担心AI与创意活动有关?“我不觉得受到威胁。相反,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解脱了。这听起来可能很刻薄,但从我的审美角度来看,作曲家只有在起初缺乏真正的创造力时才会被AI威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于任何艺术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对艺术自我的理解局限于重新排列公式或已建立的表达方式的小碎片——称之为音乐材料,称为图像构成或其他——那么AI可以自动化这些,并且我们实际上不需要那些作曲家来生产这些东西。
“AI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跳出框框思考——字面意思是,因为它被困在里面。这是它自己的监狱。而我理解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打破这些监狱的栏杆。也就是说,我的工作是思考音乐除了现有的形式之外还能是什么。不是复制我们所知道的音乐是什么和已经存在的音乐。那不是我的工作。那令人乏味。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思考我们可以开辟哪些其他的音乐体验路径。”
4月25日,星期五,马科尔将在周四下午会有一场讲座,也就是4月24日。
(以上内容均由Ai生成)